陈来:“文化热”中,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
2018-10-25 08:37:00 作者:陈来 来源:人文思享公众号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作多种,除三联书店已出版的“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东亚儒学九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回向传统》、《仁学本体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等。
(口述/陈来采访、整理/艾江涛) 原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2018年10月8日,总第1007期)
我是1978级研究生,“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们一般讲到1977、1978级都是指本科生,这两届本科生加起来将近40万,第一届研究生比较少,社会上关注不多。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代人学术历程开始比较早。1980年,我已经写完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我们那会不分硕士生博士生,大家都认为自己相当于苏联的副博士。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先生是我的导师。他那会给我们上两门课,一个是《史料学》,一个是《方法论》。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没有机会上课。老先生1978年开始给我们上课,都是准备了几十年的课程,很多人都跑来听课。两年后他由于突发心脏病,就没法上课了。改革开放后,冯友兰先生在解放前出的书,我们也能看到了。有人总结我们这批人,听张先生课,看冯先生书。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接续上了解放前的学术传统。
比一般人幸运的是,我在1985年博士毕业后,一直当冯友兰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90年去世。这段学术因缘,非常难得。
1985年,“文化热”兴起。应该说,是多种因素凑合的结果。当时,改革推进到某个阶段,遇到一些问题,主政者有一种观念,认为是文化出了问题。包括之前对“文革”的总结,认为根子在封建主义,这成为80年代初的一种共识。任继愈先生在批判的意义上,认为儒家就是儒教,就是受此影响。主政者的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研究。
也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1984年底,中国文化书院成立,1985年1月,开办第一期讲习班。那会谁听过冯友兰、梁漱溟这些老先生讲课?当时影响比较大,带动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反思。1986年以后,文化书院开始搞函授教育,面向全国成千上万人,这个面一下就广了。导师不仅是老先生,还请了杜维明、陈鼓应等海外学者,对大家很有吸引力。
还有一个线索,这个时候,大家越来越明确,改革开放所引导的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1985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1986年12月10日,编委会和三联书店在《光明日报》登出半版书讯广告,讲到《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出版计划。这对于学界震动很大,带动了大家对西学的翻译介绍。现代化理论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列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在1987年出版。
还有一股力量,稍早一年,就是从1984年开始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并非严格的学术翻译,基本采用编译的“短平快”的方法,介绍西方学术,包括历史、人文,但更多的是与科学相关。由于抢得先机,在当时大学生中影响非常大。
1987年,我在《思想出路的三动向》一文中,讲过这三股力量。“走向未来”丛书,强调科学精神;中国文化书院,注重传统;“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注重文化关怀。所以“文化热”,包含了不同力量,以这三股力量最有代表性。
回头来看,80年代的“文化热”,与80年代初的一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动员期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即使在比较偏重传统的中国文化书院,当时也有批评儒家最厉害的包遵信等人。
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人,大都是我们学校教研室的,因为1984年我还没毕业,就没有参与。反而参与了以北大、社学院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
1986年,我把博士论文朱子研究的书稿交付出版社后,便到哈佛大学开始为期两年的访学。虽然不在国内,但我一直关注着国内仍在发展中的“文化热”。
出国之前,我对传统与儒学的态度,和大家差不多,虽然不是全面反对,但也有批评,认为传统文化不注重个人权利。在国外那两年,一开始主要是受到杜维明先生的影响。杜先生1985年在北大教了一学期课,在当时的讨论中带进来一种声音,有人为儒学说话,不全用激进主义的态度看待儒学。在美国我们的交流比较多。另外,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我注意到,基督教的传统无处不在,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仍然能做什么?
所以那段时间,我的认识发生了转变。1987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开始讲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那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点是,最早提出了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肯定。文章针对的是当时的改革问题。当时有些理论家居然提出“一切向钱看”的口号,我那时就强调,“一切向钱看”,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传统。
在1988年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其前景”国际研讨会上,我又提交了一篇论文《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那次会议上,海内外学者坐到一起来讨论儒学,是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我那篇论文,一方面针对包遵信的文化激进主义发言,一方面针对韦政通、傅伟勋等人希望将儒学改造为包打一切的方案的全面改造论发言。我记得,在新加坡开会的第一天早上,包遵信就说:“你的文章是针对我的。”
他们认为以“伦理本位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且在当今社会仍是政治、经济、法制的进步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此主张“彻底打破”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我认为他们是一元化思维,希望用儒学来解决一切问题,是一元化论述。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有的管这个,有的管那个,然后一起解决社会问题。儒学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为改革提出具体设计,而是提出跟改革相互补充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让儒学包打一切的一元化思维,并不合理。后来我就问:我们可曾向佛教要求浮士德精神,向神道要求民主理论,向印度教要求个性解放,向天主教要求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杜维明觉得这些反问很有力,对儒学论争非常有利。
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是包遵信,他到哪讲一句话,下面就鼓掌,时代思潮就是这样。可在新加坡的会议上,包遵信基本上不讲话,非常沉闷。回来在北大开会,又变成包遵信的主场了。他讲一句话,学生在下面鼓半天掌。在那个氛围下,极端的文化激进主义很容易变成政治的激进主义。
事实上,到1989年“文化热”的后期,多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包括甘阳,那会也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1986年,甘阳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还是讲“以反传统来继承传统”,但到后面便开始强调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性。当然是多样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止我这样,还有从别的角度进入的思考。
其中有一个契机,就是1988年赵一凡翻译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出版。丹尼尔·贝尔所讲的三元化结构,人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他拿自己举例: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社会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我觉得这给很多一元化思维的人以新的启发,自由主义者并非在所有层面信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可以和很多东西结合。
1989年,我写了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收入了林毓生所编的《五四:多元的反思》一书。在那篇文章中,我恰恰用韦伯的理论还制西化主义者。韦伯的思想是“二战”以来西方世界最流行的理论学说。韦伯虽然指出现代化是工具理性的强势发展,但他非常重视价值理性,他有悲观主义倾向,认为在现代社会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性受到抑制,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认为,“东西古今”问题的本质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我们从西方特别强调要引进的属于今的那部分,大部分属于工具理性;强调反对和批判的,大部分属于价值理性。从韦伯的理论看,价值理性不是要去除的部分,而是要建立其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合理关系。
进入90年代,有左派学者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我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人文主义的视界》,来阐释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这一从西方学术界开始使用的概念,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地、粗暴地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位、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我自己虽然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但不是被固定在这里,这是我思想的一面,我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开放的一面。
从80年代到现在,不管是在传统文化最低潮的时候,还是近些年来的“国学热”中,我始终不变的一点是,对儒学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文化形态,及其对现代化的作用,始终寄予完全的信任和理解。
采访手记 文/艾江涛
一直以来,陈来都以研究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享誉学界,事实上,他对于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也从未缺席。
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很早便有明确认识。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他便讲到当代有三种在场的儒学,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如果说在学院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属于学术儒学的范畴,那么从1987年开始,参与围绕文化儒学的讨论,则是他另外一条未曾中断的主线。
就像陈来自己所说,作1978年的第一届研究生,他们比同级的本科生更早开启学术历程。在80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更多顺着学术思潮一路前进,并非像一些学人,到“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90年代,才开始踏踏实实的学术研究。
早在1980年,研究生还未毕业时,陈来就完成自己最早的学术著作《朱子书信编年考证》。1985年,他的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对朱熹哲学思想及发展作了细密的历史考察,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研究成果。1986〜1988年在美国期间,陈来开始准备王阳明的研究计划。1990年,完成专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此后,陈来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宋明理学,出版《宋明理学》等著作。1991年之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入古代思想研究和现代哲学研究,完成《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孔夫子与现代世界》等论著。
1985年,“文化热”兴起。在这场推动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陈来不仅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重要成员,还以一系列文章,参与当时的文化论争。
在写于1987年的文章《中国近代思想的回顾与前瞻》中,陈来最早肯定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提出“传统思想的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的判断。
在那个反传统意识占据主流的年代,陈来受到杜维明等海外学者的影响,在美国的两年访学生活,更让他坚定了对传统儒学的肯定与理解。
他一方面反对包遵信等人的全面否定儒学的文化激进主义,一方面反对韦政通、傅伟勋等人的儒学全面改造说。借助马克斯·韦伯等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陈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儒学作为一种价值理性,仍有强大生命力。“儒学不是不支持改革,但它有它的特点。光有改革不行,还要有价值和精神的补充,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的世界观来引导中国人的一般精神方向。”
回头来看,陈来当年的一些判断,在今天并未过时。对于新世纪以来不断升温的“国学热”,他早在2010年的《光明日报》上,便以《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予以回应。在他看来,“国学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对这场自发形成的国学热,陈来持总体肯定的态度。正如他多年未曾改变的判断,传统文化在现代人的心灵滋养、情感慰藉、精神提升、增益人文教养方面,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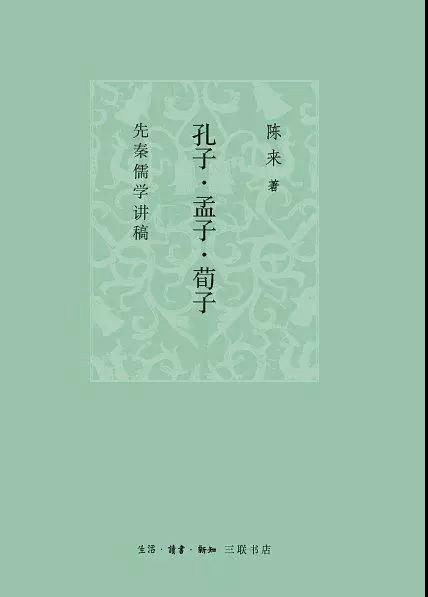
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 陈来 著

仁学本体论 陈来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