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来源:孔子研究作者:邓立 2020-10-29 1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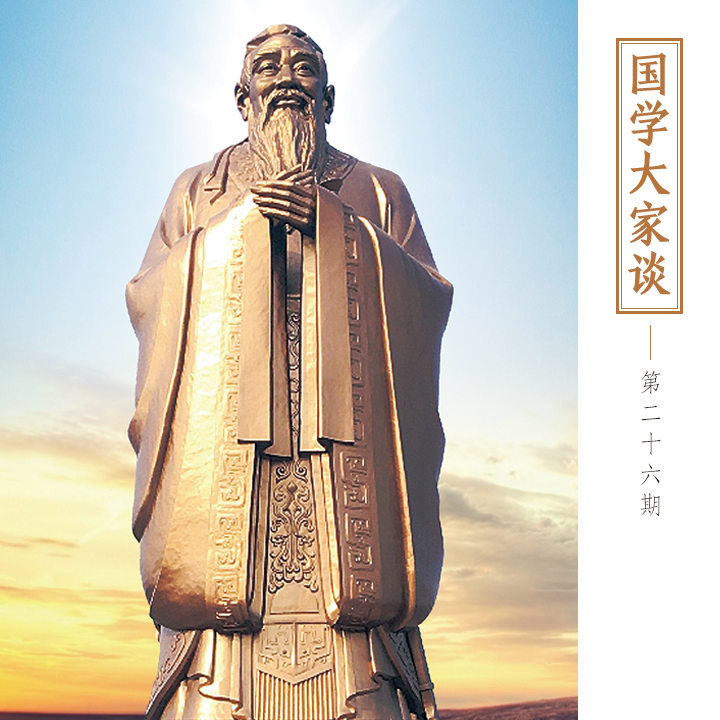
于儒家而言,“贵”不仅是以价值追求为中心的哲学范畴,而且是趋向于人格美善的伦理观念。儒家伦理,既有仁、义、礼、智、信、忠、孝、诚、节等显性的道德范畴,也涵括诸多具有伦理意蕴且与道德规范辅车相依的价值理念。“贵”即为这样一种典型的与传统道德内在契合且具有丰富伦理意蕴的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贵”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儒家把“贵”视为理想人格所期待的、现世的存在样态,“贵”是道德人格的追求,也是精神价值的彰显。这一人格和价值强调的是精神领域,由此延展到人们对于道德品质的诉求尤其是美德的崇尚。从字源、词源的界定看:“贵,物不贱也。从贝。”“贵”的本义,主要指向“物”及其价值;“贵,尊也。”“贵”通常与“贱”相对而生,兼具价格与价值之义,又凸显人的身份和地位。“贵”的观念因引申而在传统文化中意蕴丰富,并实现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贯通。但是,在宗法制度背景下,“贵”的角色和身份在社会中存在明显的缺陷和错位,似与孔孟所构建的“仁政”、“王道”的理想社会相悖。戴震曾以“理”为中心揭露了这样的社会怪现状:“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明显地,儒家理想之“贵”与现实之“贵”是存在分殊的。那么,儒家视野中的理想之“贵”有怎样的价值考量呢?围绕这一问题,本文拟从个体人格、人伦关系、道德风尚的层面来检视儒家传统“贵”观念所蕴蓄的伦理维度。
一、个体人格之“贵”
儒家思想中,道德人格塑造最核心的便是君子人格。“贵人”之“贵”作为一种人格属性,于相对应的主体而言,它的行为实践具备君子的特质,其表现往往在于“义”举。此“义”对于它所作用的对象来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符合正义的人格“善”。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换言之,个体人格中“贵”的前提是恰当把握“义”这一价值准则。从道德人格方面看,“贵”属于主体道德的现实表征。 依此逻辑,道德人格之“贵”应表现为对善的崇尚。事实上,这也是传统价值观原本赋予“贵”的理想和诉求。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本质上是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取得平衡的道德人格,它以精神价值为核心,彰显个体人格之“贵”。具体而言,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个体人格之“贵”可从三方面加以检视。
一是个体人格之“贵”的价值属性。儒家认为,在整个有生命的自然世界,与“物”相比,人有其独特性,这便是人之“贵”。当然,人之“贵”不仅是因为人作为鲜活的、有灵性的生命存在,而且在于它是以道德人格的方式来呈现的。 《孝经·圣治》借孔子之言云:“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在哪? 荀子阐释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荀子·王制》) 进一步说,人存在于伦理关系之中,人有道德属性,表现为仁、义、礼、智、信、忠、孝、诚、节等等。以道德规范指导实践,人的价值得以体认。 张岱年先生认为,“古代所谓‘贵’,即是今天所谓‘价值’。肯定人贵于物,即是肯定人的价值。” 一致的看法有,儒家肯定人是万物中最“灵”的也是万物中最“贵”的,“贵”是指人性中的价值内容。儒家强调的“贵”,定位为“价值”,无需置疑。诚然,以人的固有属性为视角,“贵”的内核应该聚集为道德价值,进而内化为理想的道德人格,它兼具价值属性和道德属性。换言之,儒家往往是从人有别于人之外(物)的角度来定位“贵”的价值的,中间包含了道德的情怀和伦理的考量。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并非是以人之“贵”来否定“物”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在于凸显人的道德属性、道德意识以及道德品质。 儒家之“贵”,“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 (《礼记·祭义》) 而这正是儒家人格塑造的根基,同时也是以价值属性来定义个体的道德人格。
二是个体人格之“贵”的价值彰显。“贵”的价值包含了一种能力的维度。能力的彰显,绝非仅仅局限在物质利益的创造之上,也必然体现在道德人格的养成之中。儒家之“贵”,应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而在这个综合能力中,个体人格的涵养及表现无疑成为是否彰显“贵”的价值标准。荀子云:“高尚尊贵不以骄人。” (《荀子·非十二子》) 按此意思,尊贵之人或“贵人”应该是低调的有德、有能之人。所谓“贵人”,有对象的相对性,它往往存在于特定的两个主体之间。对于“贵人”的人格期许来讲,其形象往往是君子。正如荀子所引古语:“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 (《荀子·非相》) 其中包括了传统的价值观:贵即好,好即善。这似乎是认同广泛的逻辑。 儒家之“贵”,从人格形塑起始,就内蕴美好、良善的品质。而且,此道德品质容易获得认同,有较强的带动力和影响力,能起到示范、传承作用。 “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 (《仪礼·丧服》) 在此,《仪礼》把“君”与“贵人”视为道德人格的价值共同体,“贵人”实为贵族,这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伦理观、价值观。在古典价值观中,“贵人”,一般指两类人:一是有地位、权势之人;一是品行高尚之人。当然,两者并不必然兼顾和并行。而在儒家的视野中,品行高尚的“贵人”应注重“节”德的持守,其人格特质往往通过讲仁、尊礼、行义等德行而呈现。仅就这一层面,“显贵”是个体人格的动态表征,其中,“贵”的价值在于它可通过主体的人格培育和道德实践而得到彰显。
三是个体人格之“贵”的价值诉求。儒家之“贵”是在精神信仰基础上体现出的社会关系中主体的人格形象;“贵”呈现的也是一种独具特质的价值观念。儒家期待通过这种主体形象和价值观念去引领积极价值,聚合正能量,形成良好风尚。这个过程,主要是由“君子”这一主体来完成。作为理想人格培育的一个目标,“贵”既是个体道德人格的彰显,也含有人格外向超越的意味,成为一种预设的或既定的道德人格之理想与诉求。如荀子所论:“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 (《荀子·不苟》) 其中的“贵”,不仅是可贵,而且有君子在道德实践中对于人格完善的价值考量。人的行为、言辞、名节等,通过德性与德行的互动来体现“贵”的品质。又如:“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荀子·大略》)于此,王先谦认为:“修德在己,所遇在命。”“贵”在修德,君子作为儒家形塑的理想人格,有明确的价值诉求。对儒家而言,祈求“富贵”,是物质的考量,更是精神的期许。“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渊》) 如此之“贵”,似乎蕴含宿命论的意味。从价值的层面讲,儒家赋予理想人格的“贵”观念其指代意义在精神的领域。明乎此,便可认识儒家顺遂天命的态度并非宿命论所能简单定义,它至少包含了精神追求和现实考量的双重维度,而精神的维度才孕育了终极的价值。可以说,个体道德人格之“贵”本源上就是以精神为中心的价值诉求。
然而,在传统社会,“贵”的角色、身份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而儒家所谓的“贵”,以人的道德品质为根基,有明确的人格特质,特别注重精神价值的建构。于是,从价值来审视个体人格,“贵”保持着某种高度,这样的高度通常以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实践来加以衡量。儒家重视个体人格培育,首要的是重视人的德性养成,德性关系着人的价值彰显。“只有德性之心,见人之尊贵。”换言之,人之尊贵在于人有德性之心,这仍然是个体人格之“贵”的价值和道德属性。儒家道德生活的理想通过个体人格的完善来实现,是通过德性及德行对人格及其价值的肯定,实为儒家之“贵”的根核所在。
二、人伦关系之“贵”
“人伦”在儒家思想中包含了尊卑长幼等关系,又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以伦理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便是儒家所谓的“人伦”,它涵盖了传统社会最核心而又最系统的社会关系。在传统意义上的人伦关系之中,尊、卑、贵、贱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其中除了政治身份意义上的等级差异外,还涵括伦理道德关系中的人格定位。儒家思想中的人伦关系之“贵”,属于个体德行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孟子有云:“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孟子·万章下》) 在这里,因为“德”,长幼关系、尊卑关系、朋友关系得以平衡,趋于合理。另一种关系,如:“贵贵为其近于君也。”(《礼记·祭义》) “敬”成为“贵”的价值彰显应该具备的基础性条件。可见,“贵”是作为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构成的核心价值,即是通过主体的德性与德行构筑起来的价值。 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之中,儒家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价值支撑,并存在独到的伦理考量。
其一,人伦关系之“贵”逻辑地尊乎“礼”。儒家之“礼”属于维系人伦关系的核心内容。“礼也者,贵者敬焉。” (《荀子·大略》) “贵者”,作为一种角色和身份,以“敬”的方式来尊“礼”。可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贵”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其所处的身份对于角色伦理的塑造极为重要。在尊卑关系的定位中,“贵”成为一种愿景,人们以尊贵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君子作为儒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格象征,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实践中,其“贵”的身份通过“礼”得以彰显。“贵”是道德情感的寄托,也是世俗伦理关系中的理想和希望,在具体境遇下还体现一种责任担当。“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在这里,“贵其身”之“贵”是道德人格之“贵”;尊乎“礼”不仅要“贵其身”,而且还表现在“能及人”,这便是人伦关系之“贵”了。应该说,儒家之“贵”内含信念、承载希望,由“贵”的价值诉求到“礼”的伦理秩序,其中涵括的更多的是伦理道德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推扩至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多层级关系。
其二,人伦关系之“贵”关键在行其“义”。“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四制》) 这是基本道德原则。不仅如此,儒家之“义”融合了更为广泛的人伦关系。“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荀子·大略》)王先谦释曰:“此五者,非仁恩,皆出于义之理也。”从伦理关系的视角来讲,“贵贵”是主体的德行,是礼义规范指导下的人伦实践。当然,“贵贵”于此所强调的亦是“义”的道德价值,既是主体的“羞恶之心”,又表现为“见利思义”的道德人格。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中,荀子云:“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 (《荀子·非十二子》) 通过具体的伦理身份、道德境遇来审视,人伦关系之“贵”即在于践履儒家之“义”,其价值可得到更好彰显。这就是“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贵”的道德价值在人伦关系中如何得以存续?关键就在“义”。“君子不贵,教以义也。”在这里,“君子”就是所谓的“贵”的身份,“不贵”则指不以“利”为贵。质言之,“义”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它是主体在人伦关系中“贵”的价值是否能彰显的关键。确切地说,“贵”在人伦关系中如发生价值选择的错位,需要通过“义”德来补缺。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之“贵”,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道德示范才能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实现从“教以义”到“行其义”之间的互动与切换。
其三,人伦关系之“贵” 根基在辅以“仁”。儒家之“贵”在人伦关系中彰显其价值,离不开“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仁”是体现“贵人”之“贵”的道德品质。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进而言之,以仁义之心去促成人格美善,是儒家的理想。“己”与“人”在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全然不是对立的存在,在人格上是对等的关系,进而可构成一种价值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孟子云:“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孟子·万章下》) 朱熹注曰:“此言朋友人伦之一,所以辅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为诎,以匹夫友天子而不为僭。”“辅仁”对于朋友一伦,意义非凡,它能消解等级、身份的差异,实现“贵贵”与“尊贤”在价值选择上的平衡。应明确的是,“贵”的核心在于人的价值彰显,人的价值彰显是基于人的德性和德行而来,而德性与德行以人伦关系的呈现样态为表征。而且,儒家虽以人为“贵”,但其伦理考量绝不限于人伦关系本身。“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礼记·中庸》) 儒家之仁,既是人之德性,又贯通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之中。“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即是以贵“仁”为前提的,这不仅是人的价值,更是人独有的品质。唐君毅认为,“惟人有此无所不爱之仁,然后人心通于天心,为宇宙之至贵而存在。”以“辅仁”的方式为基础,建构成人伦关系之“至贵”,是儒家的理想和追求。质言之,儒家之“贵”的价值,根核在“仁”。
从根源上看,儒家之“贵”属于交织着理想与信念的价值观。在理想的人伦关系中,“贵”俨然就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美好人生的追寻,当然它包括由人的德性养成到道德实践的完成这一全幅过程,是自觉修养到主动行动。从“德福一致”的层面而言,追求“贵”与追求幸福同样重要,甚至追求“贵”就是追求幸福的道德生活。 孟子讲:“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孟子·万章上》) 明乎此,便能理解儒家之“贵”的价值彰显,其存在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即是从个体人格之“贵”到人伦关系之“贵”的推扩、延展,这亦是构成崇尚“贵”的价值观念这一传统社会风尚的重要因素。
三、道德风尚之“贵”
儒家在个体人格、人伦关系的维度对“贵”的价值有独特定位,与此同时,期盼“贵”能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这个理想的状态就是通过道德典范的作用不断影响、带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德性的培育到榜样的塑造,儒家注重的是典范的力量,期待形成人心向“贵”的社会风尚。当然,这样的社会风尚必须是符合伦理道德的,而且只能通过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来实现。可以说,儒家将具体的道德实践到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共生视为最优的伦理生态,而且始终以道德教化、德性养成的方式来追求这一理想社会的实现。此由儒家对于“富贵”之“贵”与“良贵”之“贵”的价值诉求可见一斑。
一方面,儒家肯定“富贵”的生活。《周易·系辞上》云:“崇高莫大乎富贵”。古人一般也认可富贵是道德生活达到极致的表现。社会风尚之“贵”从“富贵”的生活样态开始。儒家注重精神价值,但不排斥对物质的拥有。因此,“富贵”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礼记·中庸》云:“素富贵,行乎富贵”。“富贵”的生活状态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中庸之道的志向。孟子揭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欲贵者,人之同心也。” (《孟子·告子上》) 诚然,“贵”在这里主要指有志于“道”而能以仁义为准则之人,这才是“富贵”应该呈现的合理样态。儒家通过强化“贵”的价值,尤其是“贵”的道德价值,由个体需要到群体诉求,希望形成人人竞相向“贵”的社会风尚。要强调的是,儒家理想中的“贵”并非全然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权贵”,而是内蕴着道德品质的“尊贵”的理想人格。周敦颐《通书》中的阐释较为明确:“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显然,在这里将尊贵之“贵”所达到的高度直接与人的道德品质等同起来,不仅强调“贵”的人格,而且还追求更高的境界。这种包含了更高人格境界的“尊贵”成为人们竞相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对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比较而言,如果说“尊贵”是道德人格的表征,那么,“富贵”其实仅属于具体的生活样态。在儒家的视野中,无论是尊贵之“贵”,还是富贵之“贵”,都是以“至贵”为终极目标的。从价值观念到道德心态的转化,以此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是儒家思想的预设,也是文明进程所期待的方向。“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礼记·坊记》)所谓富贵之“贵”,是由物质满足到精神的提升,核心在精神领域,“孔颜乐处”可作一注脚。根本上讲,儒家的教化首先在于价值观的塑造。“富之”、“教之”(《论语·子路》) 的理念很明确,孔子注重的是“富贵”而有德,以道德教化作为根基,肯定个人、家庭、社会对于“富贵”的期盼和追求,是“家国天下”的全幅考量。无论是对物质的追求,还是精神的提升,其目的都是为了以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建构具有良好道德风尚的理想社会。
另一方面,儒家崇尚“良贵”的品行。何谓“良贵”?孟子首提“良贵”的概念,朱熹注曰:“仁义充足而闻誉彰著,皆所谓良贵也。”“良贵”不仅有价值属性,更是内含了道德本质。“仁义充足”是道德底色,“闻誉彰著”实为道德底色在实践中的呈现。“良贵”源于心性,是性善论的延展。在孟子这里,“良贵”与“良知”、“良能”是一体的。显然,作为个体而言,“良贵”是具备“良知”、“良能”的德性,由“良贵”的德性转化并扩展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公德)正是儒家所理想的不断拓展而富有实践张力的道德世界,是以“仁义”为核心形成的具有良好社会风尚的理想世界。孟子所谓的“良”,就是善,虽然“贵”并不能全然成其为“善”,但传统价值观中的“贵”亦往往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好”,继而在实践中展开为普遍的对于善的崇尚和追求。王阳明曾讲:“吾所谓重,吾有良贵焉耳,非矜与傲之谓也;吾所谓荣,吾职易举焉耳,非显与耀之谓也。夫以良贵为重,举职为荣,则夫人之轻与慢之也,亦于吾何有哉! 行矣,吾何言!” 儒家之“贵”作为一种价值的定位,对于社会风尚而言尤为重要。王阳明的观点很清楚,唯有通过“行”———道德实践,才能彰显“良贵”对于社会的价值。“良贵”为社会大众所期许、追求、践履而形成风尚,紧扣着“德福一致”的价值观。社会风尚中积极价值观的应有之义,莫不有如:“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返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这是“贵”的另一种高度、状态或境界。与儒家之“贵”相比较,它似乎缺少了伦理道德的意蕴,却包含了更多的价值哲学的考量。于此,亦能体现“贵”的观念对于社会心态塑造以及道德风尚引领积极的一面。 换一个视角:“富不侮贫,贵不傲贱” (《墨子·兼爱中》) 作为应然层面的社会道德,与儒家对照可见,传统的主流思想对于社会风尚的导向乃至终极价值的期待是高度一致的。
确切地讲,无论是“富贵”的生活样态,抑或“良贵”的品德声誉,似乎都不足以承载儒家对于“贵”的期冀。儒家的理想是,以人格典范的力量为根基,塑造无数具备“富贵”和“良贵”双重特质的道德主体,促进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可以说,儒家之“贵”,是一种价值,更是一种精神,是“伦理至上”的核心精神。这样的核心精神昭示着:“贵”的人格,祈盼“富贵”,崇尚“良贵”,追求“至贵”。《礼记·坊记》有云:“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如果仅从这一层面的定位来看,“贵”所换来的礼让谦和的社会风尚以严格等级界限为前提,无疑属于宗法制度的固有弊病。而与此并行的是儒家思想理论所建构的维度:良好社会风尚之形成可印证“贵”的价值,正如《汉书》中描述的伦理生态:“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于此,“人之贵”,应是从人格到人伦再到风尚的形成这一不断扩充的过程,是儒家所孜孜以求的由个体到家庭到社会的“天下一家”、“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生态。这样的社会生态,于个人,人格与品质相辉映;于社会,秩序与伦理相吻合。“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 ;应该说,儒家对于“贵者”有更高的道德期许。从理想人格来看,“贵者”,应该既是修身律己的表率,又是崇德向善的榜样,更具礼让宽容的形象,这就是所谓的典范。儒家认为,只有树立道德人格的典范,以此为根基,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当然,儒家的典范从圣王开始,是自上而下的。 这是历史的认知,也是现实的考量。 正如王阳明所说:“为人上者,独患无其诚耳。 苟诚心于振作,吾见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风者也。” 这与“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的德政思想一脉相承。上行下效的典范作用,是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的内生驱动力,追求和崇尚“贵”的精神价值的典范,所产生的是道德风向标的意义。
余 论
如何检讨儒家之“贵”?似乎是更受关注的问题。儒家之“贵”,主要为精神价值的一种存在样态。无论是在个体人格、人伦关系抑或是社会风尚中,“贵”作为价值彰显的方式,其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到个体人格的道德判断,进而延伸到整个人伦关系之中,逐渐形成一种被普遍崇尚的社会风尚。这亦是儒家的理想和追求。而现实中,“贵”却呈现出正负价值的两重性,其表现的几个方面应该正视。
首先,“贵”观念的价值旨归值得肯定。儒家之“贵”的价值建构是理想性的。它在宗法制度背景下侧重强调人本身的“贵”,而较少论及等级差别之“贵”。于是,“贵”成为一种价值取向,是主体价值彰显的根本旨归。由伦理道德的指向而言,“贵”的内在价值可呈现为对美好的追求,是理想人格的重要符号和标签。儒家所强调的“贵”,是对于道德人格培育、人伦关系建构、社会风尚引领的期待。因此,本源意义上,“贵”承载的是人本身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价值。在原始儒家的视野中,“贵”既是好的,又是善的,也是幸福的表征。 回到孔子,将“不义”之“富”与“贵”视为“浮云”,这才体现出儒家根本的价值追寻。
其次,“贵”观念的历史缺陷不可回避。当“贵”作为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时,其缺陷属于历史性的。而缺陷的根源在于不能脱离宗法等级制度。 宗法制度下的固有语境是:“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等级制度导致“贵以袭贵”的价值观进一步地异化,形成扭曲的循环模式;制度的不合理性,促使对“贵”的盲目崇尚或膜拜成为理所当然,转而演变为社会中不平等关系的助推器。由此与孔孟所推崇的纯粹道德人格意义上的精神价值之“贵”存在根本性偏差。无疑,这样的历史缺陷,需要从人格培育、风尚引领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检讨。
再次,“贵”观念的实践错位必须矫正。“贵”观念导致主体的实践错位是现实性的。此现实是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现实。儒家之“贵”所预设的理想人格与社会现实之“贵”往往存在差异,理想与现实的差异直接导致主体之“贵”在实践中发生错位。 传统社会,“贵”的主体就不乏有其特殊性:“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 (《韩非子·孤愤》) 、“贵人,非所刑也” (《春秋穀梁传·襄公二十九年》) 。作为一种身份、角色之“贵”,游离于伦理规范、甚至法律准绳之外,失去约束,“权贵”亦由此形成。在当下,唯有完善德治与法治体系,弘扬平等、公正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矫正“贵”的实践错位。
要而言之,传统“贵”观念根植于传统社会之中,人们重视这一价值观,是其价值具有巨大张力的表现。而现代意义之“贵”,在坚持以精神价值为中心,培育道德人格,建构良好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的同时,内涵更应该具有现代性,指向应更加丰富和多元。这也正是“贵”作为传统价值观现代传承与转化的重要考量。弘扬“贵”观念的积极价值,关键是牢牢把握住“贵”的核心精神。儒家之“贵”的核心精神在于:注重个体人格的培育、人伦关系的维护与道德风尚的营造,以此构建以精神价值为中心,以人格美、风俗正为指向,以“家国天下”为“贵”的理想社会。“富贵不能淫”(《孟子·滕文公下》) 始终是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及伦理底线,这一原则和底线的根核即为可安身立命的“良贵”。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为此而追寻。
作者:邓立,贵州财经大学阳明廉政思想与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法学院副教授
编辑:解放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