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 康良:儒家文化的价值及其传承——方朝晖先生访谈
来源:《走进孔子》杂志作者:方朝晖 康良 2025-02-09 14:21
康良:方老师好,感谢拨冗接受我们采访,现就几个问题请教如下。首先,您对古代儒士有何看法?比如他们对古代文明做出了什么贡献,或者存在哪些不足?

方朝晖先生
方朝晖:“儒士”这个词出现于战国时代、儒家兴起以后,本义并不一定指在朝廷担任官职的士大夫,可能包括一切信奉孔子或儒家学说的学者,故又可称为儒生、儒者、儒家,甚至简称为“儒”。我个人觉得,儒学是一种精神信仰学说(未必等同于西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其中包含对宇宙和人间秩序的一整套看法,也包含着每个个体在人伦关系及人世社会如何安身立命的思想。对于儒家来说,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与一个人如何善尽人世的责任是一体两面、绝不可能分开的。这种一体两面的思想,我认为与儒家建立在此世取向的世界观基础上有关。正是基于此一体两面思想,历代的儒士们都认为自己承担着在人世建立秩序的使命,并以此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铸就了儒士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儒学在汉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一代代儒生几乎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真正的精英,引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总会有不少具有儒家信仰的人挺身而出、扭转乾坤,也体现在无数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担当道义、无声奉献。
儒士、儒生的身份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标记,往往是出于自我认同或后人追认,在现实生活中谁是儒、谁不是儒,从来都无法确定,这种身份的模糊性恰恰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影响广泛的现实。这一点也提示我们儒家存在及发展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其对中国传统社会作用之大。
不同时期儒生们的知识、眼界各有优劣或不足,但抽象、笼统地说他们有何不足就比较难。这是因为儒学本身不是僵化的、铁板一块的,而是包含着内在自我调适、自我更新的潜力。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在不断发展,不断自我调适。
康良:儒家道德观念的价值何在?怎样提升修养境界?
方朝晖:我认为,儒家道德观念包含着中华民族过去几千年精神思想最重要之精华,其中涉及个人修养、治国安邦、社会秩序、文明理想等一系列内容,是历史上无数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文化不断进步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是中华文明永葆活力、长盛不衰的内在秘密。当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常常把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儒学视作一种处世的精明才智,理解为成功学,这是违背优秀传统文化真精神的。
我曾在《儒家修身九讲》一书中,综合儒家、道家等思想,针对当代青年的实际处境,从守静、存养、自省、定性、治心、慎独、主敬、谨言和致诚九个方面讲儒家修养,主要关注当代人如何活学活用古代修身思想。我在书中也结合弗洛伊德等人的现代心理学成果,讨论如何面对当代人的精神心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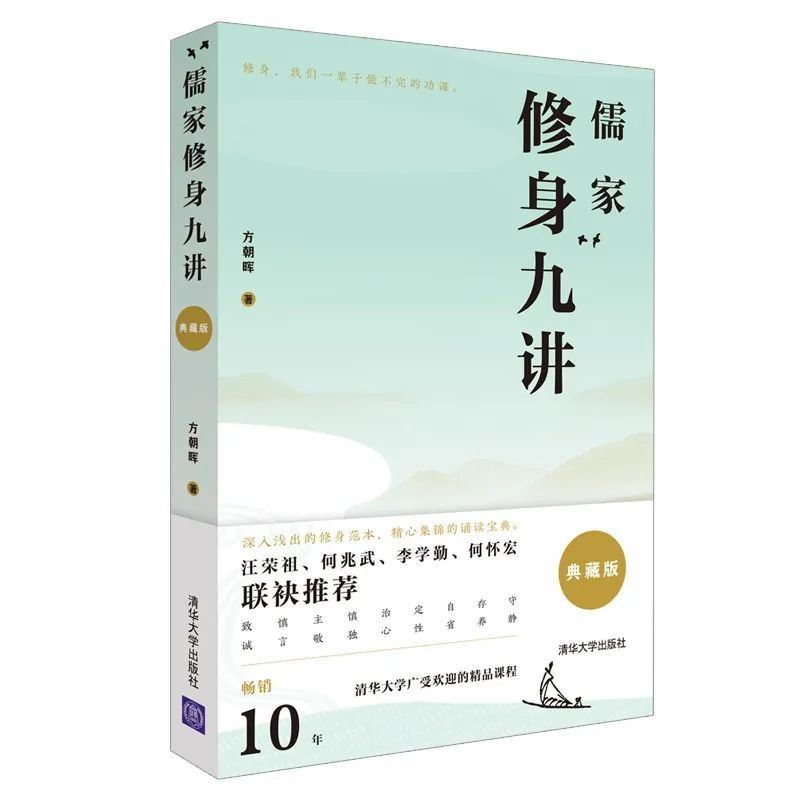
《儒家修身九讲》书影
修养主要是个人工夫,特别是包括守静、慎独、读书在内的实实在在的内在工夫。这种工夫绝不是发明若干条客观准则,人人遵照去做那么简单的,而是痛苦的自我修炼。只有从自我做起,切实面对自己,面对内心,面对各种问题,痛下决心投身其中,才可能有收获。
康良:方老师对幼儿读经有何看法?成年人是否也应当读经?
方朝晖:各大文明古国皆有自己的核心经典,它们构成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宝藏,何况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忘记本民族的核心经典,忽略祖先的思想宝库,是不能饶恕的罪过。经典的学习需要从儿童做起,但经典对成人来说也同样有价值。
对非专业社会人员来说,他们在成人阶段未必有大量时间专门读经,尽管读经定会受益。成人的传统文化基础多半是在幼时打下的,如果不从幼儿抓起,就不能真正将经典普遍推广,深植人心。
幼儿时学会的东西如唐诗宋词、经典范文等会牢记终身,也最能受益终身。幼时是成长过程中的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学会的东西对一生的心智有巨大塑造作用。把这个特殊时期用之于学习最重要的东西十分必要,而传统文化经典是其中应该学习的核心内容之一。
康良:礼学的意义是什么?能否继续发扬?
方朝晖:迄今为止,世人对礼学之于中华文明——无论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未来的——的意义认识还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过度迷信西方法治的缘故。个人觉得,礼学应当上升到中华文明制度根基的高度来理解。人类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元并存的,并且不可能都走西方现代文明的道路。就中华文明而言,我认为它建立在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的基本预设上,这种预设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带有武断性,但作为绵延了三千多年的文化心理结构,目前看不到彻底解构的可能。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华文化中有效的制度应当是以礼为基础的。事实上,人类各民族包括西方文明,都有自己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它们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指导原理,均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礼与法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制度系统,但礼的作用大于法。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重人情、轻法度,对缺乏人情味的、一刀切的制度缺乏一神教传统中那样的崇拜心理。事实上,即使在当代,制度的作用也往往要诉诸礼才能有效实施,只不过人们常常不自觉而已。就礼主要指一种不成文的、至少表面上非强制但在心理上有强大基础的规则而言,我认为它在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同样是无处不在的,并非常有效地制约着一切制度的运行(只要读一下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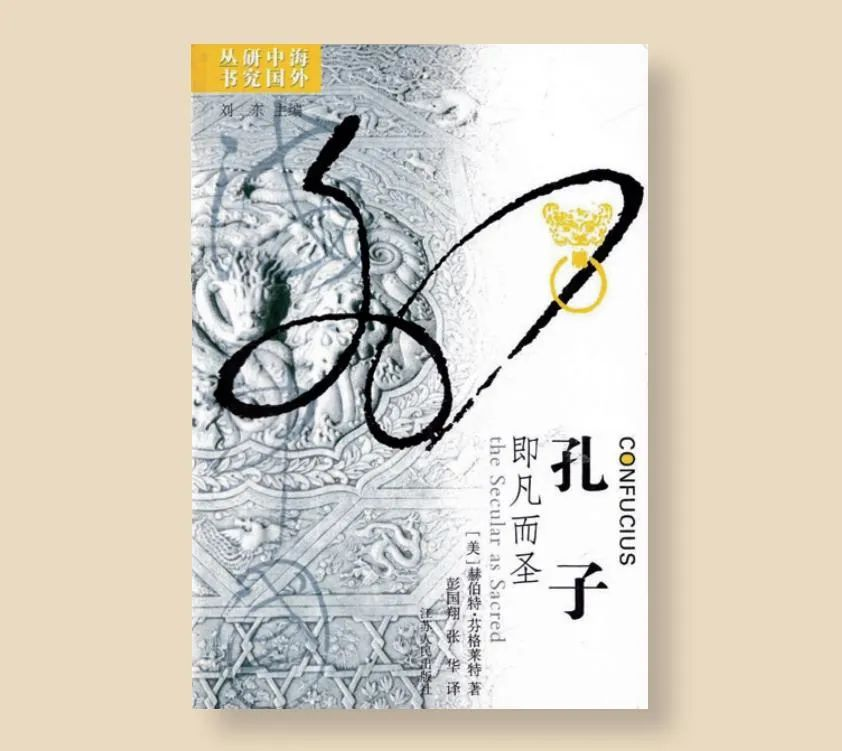
《孔子:即凡而圣》书影
就如何继续发扬礼而论,我觉得不要陷入一个误区,以为重建礼就是把古代的“五礼”等所包含的仪节规矩重立起来,而是要深入学习和体会古礼的内在精神,全面分析现代中国社会中行之有效的“礼”在何处,需要如何塑造它们。我个人觉得从这两点出发,才能真正发扬礼学。
康良:儒家的治理之道能给予我们哪些启示?
方朝晖:儒家学说甚至先秦诸子学说的核心之一就是治理问题,也可以说是秩序问题。今天我们大概都听说过儒家治道的一些内容,比如大一统、以德治国、任贤使能、礼大于法、重视人伦、重视教化、以民为本等。这些治道内容当然在今天多半没有过时。不过,我认为我们的认识仅停留在这一步仍然是不够的。在2022年出版的《治道:概念·意义》一书中“自序”中,我曾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认为,儒家治道思想需要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基本理念出发,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这是因为,儒家治道基于它对于秩序——从宇宙秩序到人间秩序——的某种崇高理念。如果把治道仅仅理解为治理方式,它就变成了类似于工具的东西,从而大大降低了地位。我们应该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原本观念出发,来完整地理解儒家治道思想。即,治道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需要而发明出来的,而是为了实现一种高远的文明理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为任何一个特定的阶层服务,也与任何利益集团的需要无关,它致力于追求一种可在天地间永存的人类生活秩序,其中包括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人伦关系、一种以统治集体高度自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一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以及一种人民自我觉醒和道德进步的文明生活方式等。如果我们遗忘了儒家治道背后的文明理念,忽略了儒家治道预设的宇宙秩序,而将其价值贬低到对统治者有利这一工具性层面,实在是以今度古,过于肤浅和片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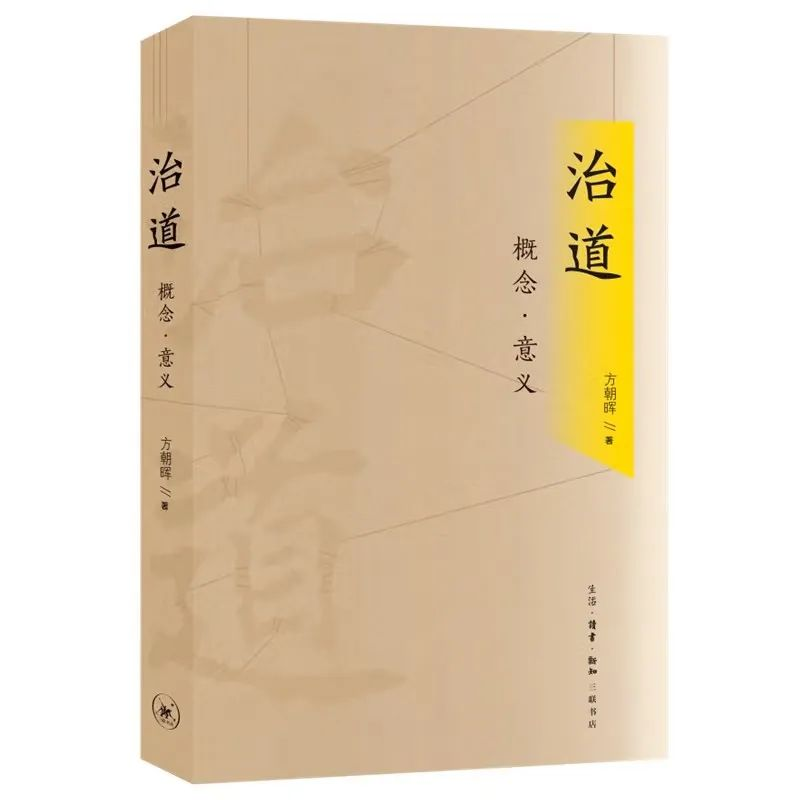
《治道:概念·意义》书影
康良:现今该如何传承儒学?
方朝晖:我认为,儒学的传承需要从孩童做起,从现有教育体制改革做起。首先,中小学教科书及课程设置需要增加相关内容,设置独立课程。目前中、小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学的了解还是主要限于语文课,儒学经典基本上被彻底碎片化,这不是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其次,将儒学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我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中国大学为何不普遍设立国学院呢?除了正规体制内教育之外,体制外的教育(私立性质的)也有待大力发展,目前政策上改进的空间还很大。
当然,儒学的现代传承远不止于教育领域,在乡村建设及城市社会建设等多个实践领域,近年来出现了复兴儒学的呼声和运动,值得引领和推动。儒学的传承和发展绝不单纯是理论和学说的问题,更是生活和实践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学的未来发展取决于真正有实践精神的儒家群体的诞生。
儒家的前提性预设是此世取向,即不以此世间之外的世界为人类终极归宿,因而它的乌托邦理想只能在此世间。这决定了儒家必然会把全面设计、规划人间秩序作为它的最高目标。这也是我认为儒学的未来传承发展要从教育特别是体制内教育做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康良: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董丽娜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