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朱子哲学与宋明理学》出版暨目录·前言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作者: 2023-05-05 16:57

《朱子哲学与宋明理学》
东方朔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有关朱子哲学和宋明理学的论集,探讨了柳宗元、罗豫章、胡宏、张南轩、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等儒学思想家的哲学思想。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始终是宋明理学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建构一种有效的道德哲学,在理论上既需要突出“自由意志”,也需要关注“共同规范”的建立,前者在为道德之作为普遍立法确立前提和基础,后者则为具共识的共同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同责任提供有效的论证和说明。设若一种道德哲学理论能够成立,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当在于它能够被人所理解;而一种理论若要被人所理解,其预设的条件之一,则必诉诸一些关于使用语言及传达意义的共同规则,“以使道德主体各心灵间具有确定的传达渠道及人所共识的规范标准”。道德哲学理论若要满足自我解释、理论解释和实践的需要,上述诸端乃不可或缺。本书所论虽散,但要旨如上。
作者简介
东方朔,本名林宏星,江西寻乌人,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出版著作有《刘蕺山哲学研究》《合理性之寻求》《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等。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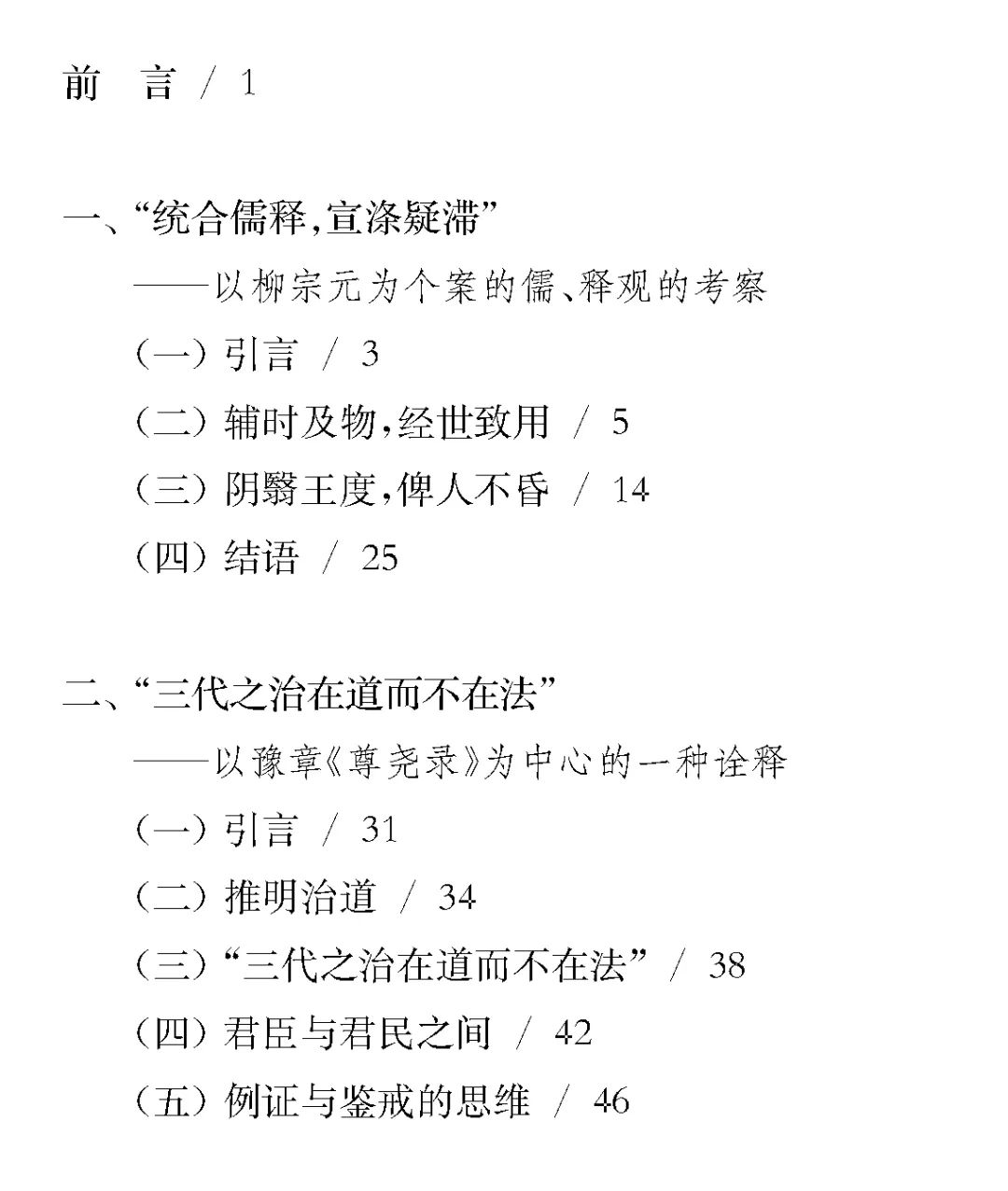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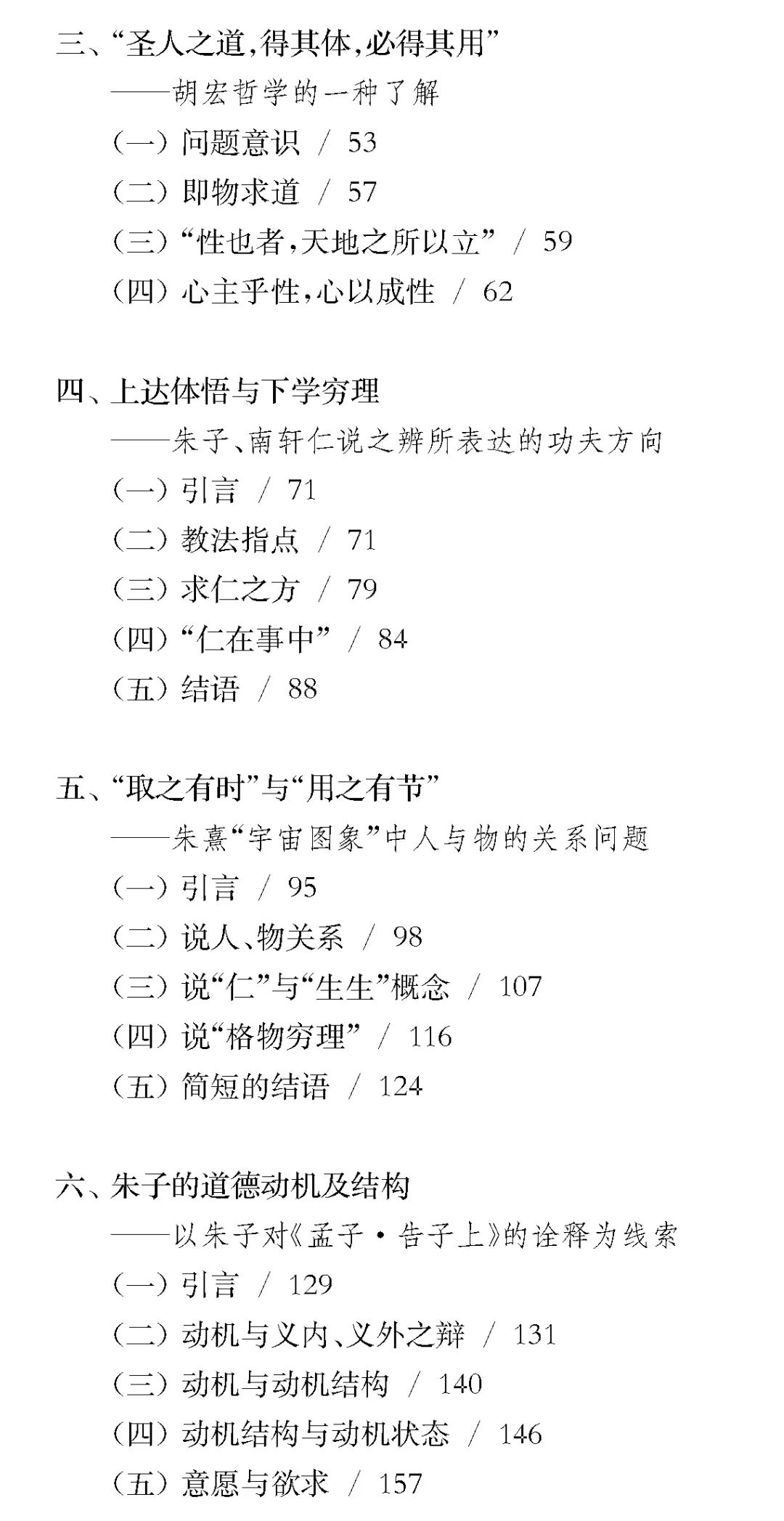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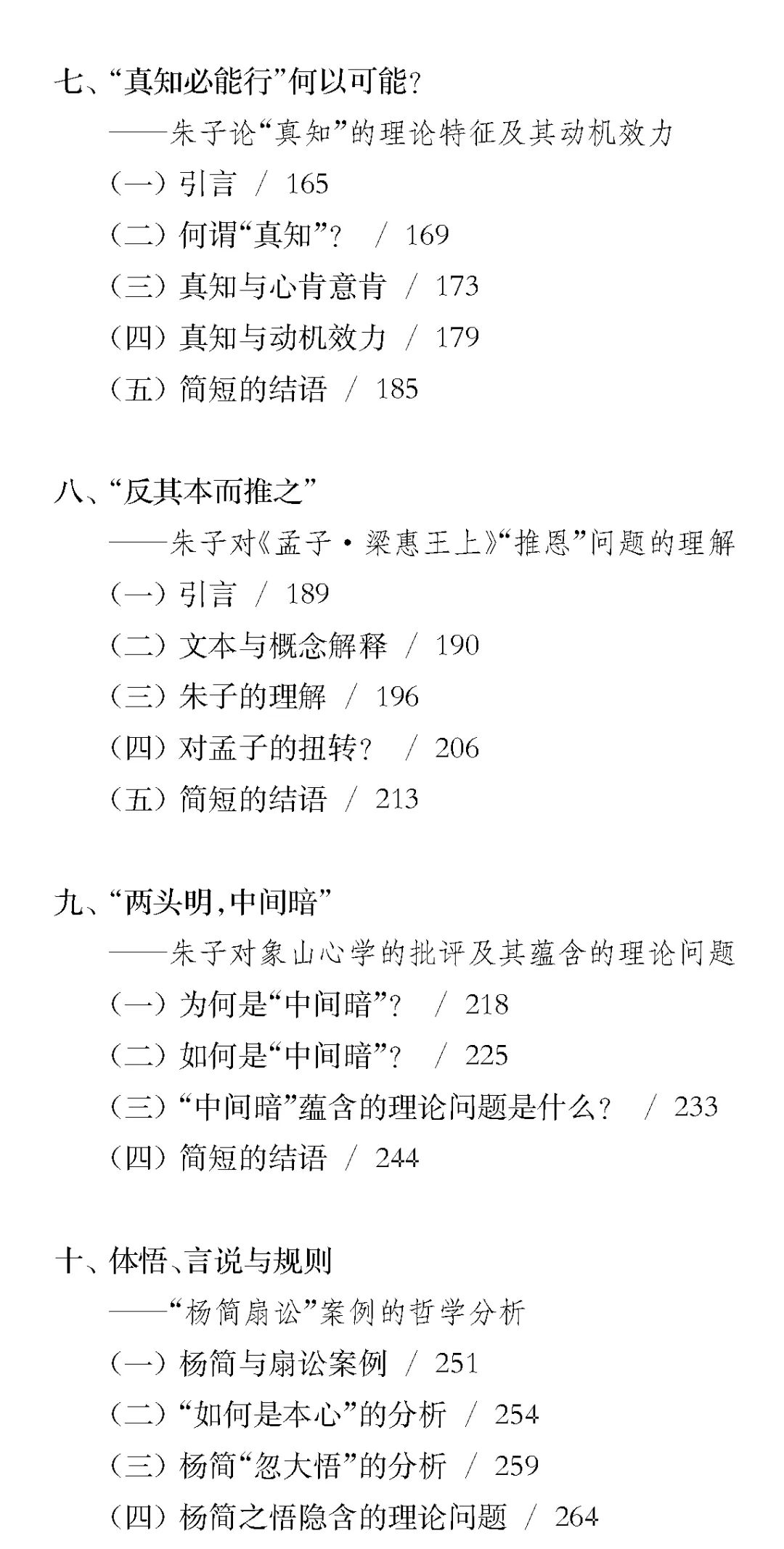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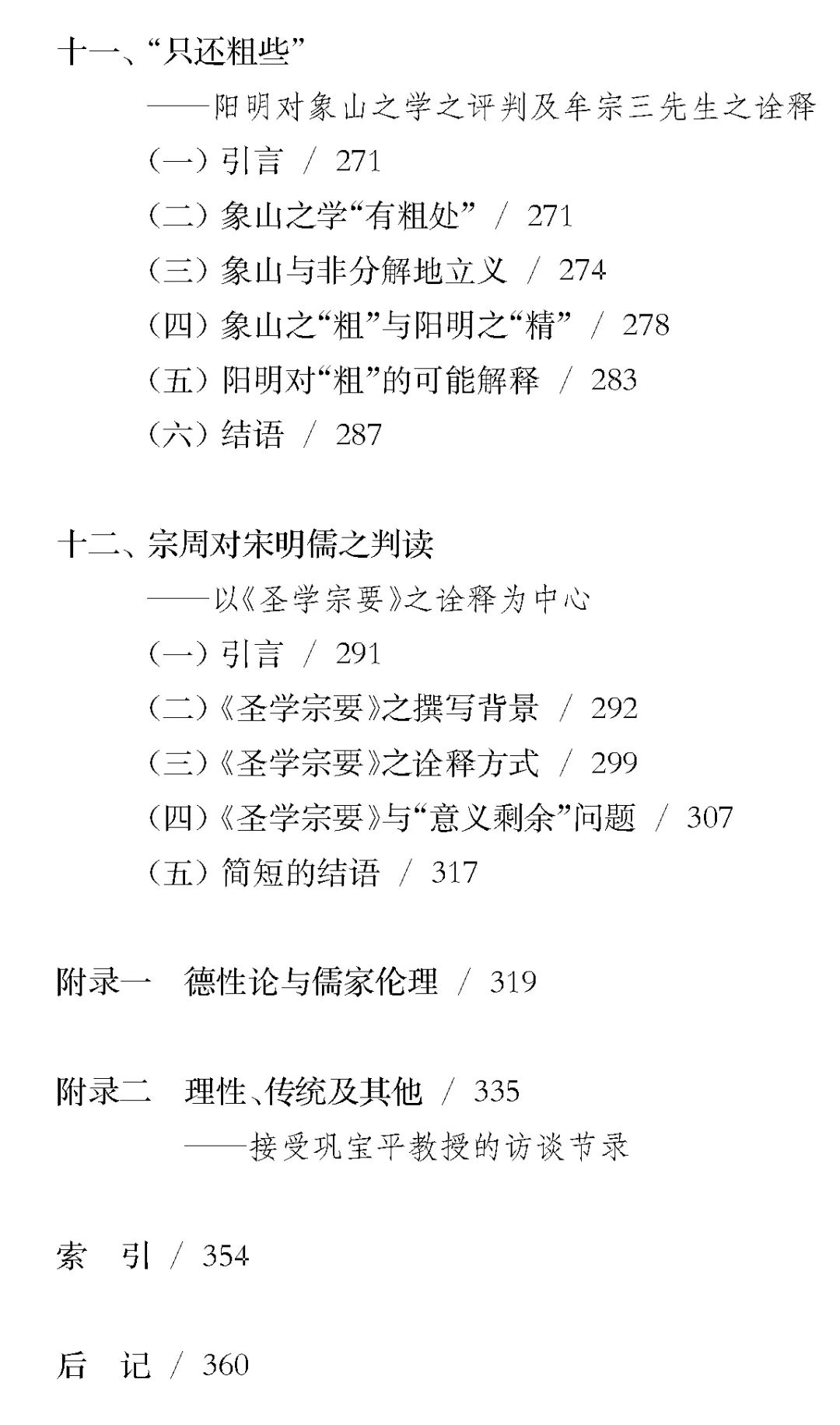
前 言
道德哲学或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意义无论如何不可低估。不过,站在现代哲学视野来看,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记得当年我在博士论文《刘蕺山哲学研究》结尾部分写了这样一段话:
蕺山以后,在心性学之造诣上已无有过于蕺山者,其所创设的微密幽深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说,蕺山结束了一个时代,此显非只是指蕺山之生命随明祚以终,而是说,心性学之发展如若无有更端别起、脱胎换骨之转换,实难以给人以一种明清可证之道德生活世界(此处所言“生活世界”与“生命世界”不可混而为一),此一论点自然见仁见智,我们亦不想在此处多加评说。
上述说法只是我个人在梳理完蕺山哲学后的一个看法,对于这个看法有两点需要做简短的说明。
其一,所谓“蕺山以后”当是指明清鼎革一段时期,在此一时期中虽学者辈出,但在心性学上却无有过于蕺山者。不过,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刘述先先生似乎并不同意将蕺山看作是宋明理学的殿军,而将这个位置代之于梨洲,依刘先生,“梨洲是在一种非预期的情况之下结束了一个时代,成为宋明心性之学的殿军,又下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转向到实学、考据文献学”。刘先生的这种看法颇有独创的特色,对我的启发也很大。1999年秋,我在结束哈佛大学的访学后,转而在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进行为期三月的访问,此时刘先生已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转任“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特聘研究员,我得以有机会向刘先生当面请益,所得甚丰,其中自然也涉及对蕺山心性学的理解。不过,我个人依然依循牟宗三、杜维明先生的主张,将蕺山定位为宋明理学的殿军。
其二,所谓蕺山以后心性学之发展需要一个“更端别起”,否则“难以给人以一种明清可证之道德生活世界”,此一说法显然是梳理完蕺山思想以后在我的心灵中留下的困惑和郁结。确乎实情的是,心学发展到极致的形态,心上功夫愈加渊深凝密,幽微曲折,“心中有意,意中有知,知中有物,物有身与家国天下,是心之无尽藏处”。不过,此心之道所托之地却始终被置于“隐”中、“微”中、“暗”中,如蕺山云:“莫高匪天,而鸢戾焉;莫深匪渊,而鱼跃焉;莫微于鸢鱼,而天渊体焉。道心惟微之妙,亦有如是者”“终日见天而不见有鸢之飞,终日见渊而不见有鱼之跃,亦见亦显,亦隐亦微”。又云:“鸢飞戾天,而绘戈不及,极于高也;鱼跃于渊,而网罟莫加,极于深也,所托之地皆暗也。”
如今看来,此“隐”“微”“暗”三字确然点出了儒家心性论中心体的根本特征,但也促使我作进一步思考:假如一种道德理论能够成立,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当在于它能够被人所理解;而一种理论若要被人所理解,其预设的条件之一,则必须诉诸一些关于使用语言及传达意义的共同规则。
然而,如果我们对本心本体只能在“暗”中体悟,只能满足于“自言”“自道”和“自成”,那么,这种理论在根本上似乎并不能满足自我解释和理论解释的需要;道德主体各心灵间若无确定的传达渠道和人所共识的规范标准,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来判定各人的体悟所包含的此是而彼非;虽悟者“深信”他与本心本体觌面相呈,但却不能说明他是如何与本心本体觌面相呈,由于其并不能提供客观的理据和规则,无法建构一套形式型知识,只是满足于自我意识的自明性宣称,因而也便无法说明自己的悟道的陈述何以为真。然而,若此处皆无,那么,儒学所极力建构的具共识的共同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同责任便难以获得有效的论证和说明。
从现代道德哲学的最新发展来看,我从不否认心学有其无法取代的价值,如坚守主体意志的自由和自决,同时也不否认心学的一套修身主张有其个人的“受用”。只不过,过分强调个人的“受用”“自得”,那么,这种“受用”“自得”与“自慰”“自了”之间便具有我们不愿看到的亲缘关系了,这构成了我为何会有学术研究上的一个转向,又为何要着力梳理朱子批评象山“两头明,中间暗”的内在原因。
无疑地,对于这样一种看法,学者完全、也一定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评,只不过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如何在理论上还“道德生活世界”以一种“明清可证”的图景却始终执拗地驱使和牵引我寻求相应的解答。此后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兴趣没有沿着蕺山以后、明清之际的线索进行,而是将重心转向先秦的荀子和南宋的朱子。尽管朱子认为荀卿之学不须理会,但学者已经指出,荀子与朱子之间其实具有很大的可比较性。
事实上,荀子与朱子之间虽然有一者主性恶、一者主性善之别,但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却在于对“心”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根本上体现为他们对“心”皆不取超越的本体意义的理解,而是对“心”采取内容意义和关联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的反省,他们均不取直觉的方式而是取客观化的方法来了解心之为心,注重儒家为学进德中必要的“过程”“环节”和“知性”,以满足建立哲学理论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到,荀子对“心蔽”的高度重视,朱子对“中间暗”的深深忧虑,都确然指向心之何以为心的再理解。
虽然他们之间相隔千有余年,但在理绪上实不妨认为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便可以理解尽管朱子认为荀卿之学大本已失,但观《语类》,朱子却对荀子论心和心上功夫情有独钟,而朱子晚年参究《大学》,对荀子的相关看法尤其心识而神会。
这是我做完蕺山之后,所以转向荀子和朱子的原因,也可以与我自己喜欢阅读具有“总结式”大儒之文字的偏好相一致。
说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起前几年李泽厚的一些说法。在《举孟旗 行荀学》一文中,李泽厚从其历来主张的“情本论”出发,提出了许多近似口号式的主张,如“举孟旗,行荀学”、“兼祧孟荀”、“朱熹是荀学”、荀—董—朱为“统治中国两千年的伦理学”等等。李泽厚的这些主张或许需要更细致的论证,而有些说法也可能会招致一些学者的不同意见,如其云:
我明确反对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也不赞成王阳明“行即知,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说。这种主张,不仅抹杀了认识的“知”与道德的“行”之间的差异、距离和问题,而且将道德视作人人具有“见父母就知(行)孝,见兄长就知(行)悌”的自然的天赋能力,将孝亲、忠君等道德行为等同于“好好色,恶恶臭”的自然生理的官能反应。这在今天如果不归之于神秘的或基督教的神恩、天赐、启示,便完全可以与当今西方流行的社会生物学合流。这与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大相径庭了。
上述说法在李氏的思想系统中或可自成一体,但也可能蕴含了很大的解释空间,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与李泽厚完全不同的解释。然而,即便如此,假如我们展望当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把“意志自由”和“共同规范”看作是一种有效的道德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或要求,那么,李氏《举孟旗 行荀学》一文提出的一些主张尽管其用词或含义有其自身的特色,但仍给人启发,甚至不乏洞见。
仅举一例,如李泽厚自己所说:“既然我站在荀子、朱熹这条线上,为什么又说‘兼祧孟荀’?既然认为朱熹是荀学,为什么又认为‘孟旗’很重要?‘孟旗’的价值、意义、功能又何在?”显然,在孟荀或孟朱之间,李泽厚有取有舍,没有一味地贬抑其中一方,至于李泽厚看重“孟旗”的实质意义,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强调应以Hume来补足Kant、非常重视道德三因素中的情感要素”。
毫无疑问,所谓“情感要素”在李泽厚的思想系统中有其特定的理解,此处不宜做具体的梳理;至于休谟伦理学和康德伦理学的长短得失,西方学界的讨论更是丰富多彩,非三言两语所可尽之。
从同情理解的角度出发,此处我们似乎不宜太过要求已近耄耋之年的李泽厚对其晚年提出的每一个命题或主张做出详细的论证,毋宁说,与其要求李泽厚就其主张提出严密的学术意义上的论证,不如说,我们更适合于透过李氏所说看到其富有思想意义的启发。假如从这个角度上看,如果我们将李泽厚的“举孟旗”宽泛地理解为突出主体意志的自由和自决,把李泽厚的“行荀学”也同样宽泛地理解为强调道德规范的理性建构和共识,那么,在过滤了各种可能的掺杂和葛藤之后,李氏的类似主张或可以显出其特有的启发和意义。
当然,如何理解李泽厚的思想,学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在思想启发的意义上,我所主张的“主体意志的自由和自决”与“道德规范的理性建构和共识”是否可以从李泽厚的相关说法中诠释出来也是可供讨论的见仁见智的主张。不过,正如上面所说的,我始终把这两点看作是建构“一种有效的道德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或要求”,这也同时构成了我自己反省传统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
人们常说,儒家的学问是一种有关“生命的学问”。记得蔡仁厚先生说过,儒家学问注重实践,而不注重知识理论的论证和概念的思辨,因为它的重点并不落在“知识”上,而是落在“行为”上。它不太着重于满足理论的要求,而是着重于满足实践的要求。所以儒家之学可以说是行为系统的学问,而不是知识系统的学问。因此,儒家主张学行合一、知行合一。因为重实践,所以儒家特别正视这个实践的主体——生命,它以自己的生命作为学问的对象,因而形成了以生命为中心的所谓“生命的学问”。我想至少从描述的意义上,绝大多数的儒家学者对于这种看法都不会持有异议。
就个人而言,我无疑也赞同这种看法。但显然,我个人的关注点似乎要低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学必须首先直面我们生存的“生活世界”,换言之,我认为儒家的伦理学可以在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生命世界”之间保持一个不断升进的过程,亦即:在如何保证人的“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的基础上,寻求人的“生命世界”的充实和完美;在如何造就一个合格的公民的基础上,提升人的君子品格和道德境界。或许就在这里,我们可以设问,假如一种道德哲学“不太着重于满足理论的要求”,“不太着重于知识理论的论证和概念的思辨”,那么,它在如何保证人的“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方面便总存一隙虚歉。
我们想指出的是,对于儒家的道德哲学而言,知识理论的论证或满足理论本身的客观性和一致性的要求,并不是舌灿莲花或快愉唇吻之事,毋宁说,它深深地关联到“儒学所极力建构的具共识的共同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同责任如何获得有效的论证和说明、在实践上又如何可能”的问题,因而构成了今日我们反省儒家伦理不可忽视的课题,这使我想起阿佩尔说过的一段话:“如果——关于纯粹主观的和私人道德的观念包含这一点——个体的所谓‘自由的’良知决断是先天地孤立的,并且如果它们在实践上并不服从任何共同规范,那么在这个由现在引发了的宏观作用的公共社会实践所组成的世界中,它们就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按照概念的严格规定,我上述所写的并不是“前言”,而只是个人的一些兴会和随感,不免缺乏论证,东拉西扯,如果任由下去,那便没完没了。所以,应该到此为止了。
编辑:张懿程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