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
2018-09-12 09:26:00 作者:丁万明 来源:中国孔子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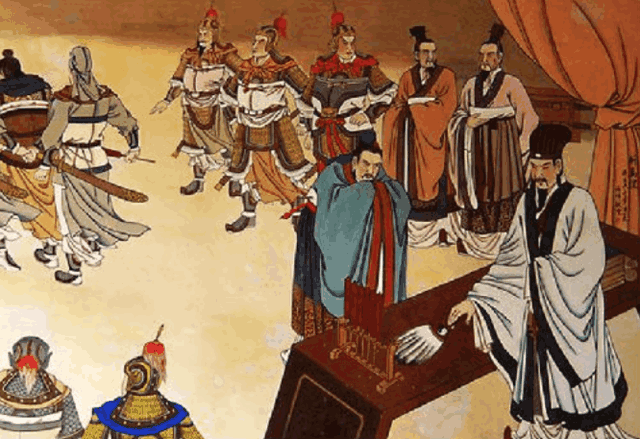
大唐名相张九龄说“治国之本在治吏”,吏治则国治。“吏治”的首要任务就是用什么人,“治吏”的实质是怎么用人。“用什么人”不仅关乎对人才的价值评判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状况下多方利益博弈妥协的结果;“怎么用人”则涉及到选官制度的贯彻实施。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制度变迁,而且导致了这一制度的变异流弊。仔细梳理下来,从察举征辟到论资排辈,再到抽签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发人深省。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一
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 千古难题谁解的
《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为政以德”,后世许多人据此认为儒家主张“人治”。今人言“人治”、“法治”,犹如古人言夷夏之大防,似乎是水火不相容之两极。荀子曰:“不患无治法,而患无治人。”康有为云:苟无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亦文具空存而已。据此而言,人在历史上的主观能动性绝对不容忽视。
在司马光看来,治国理政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因此他主张:“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他的观点与唐太宗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脉相承。问题是“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司马光认为,如果仅仅用口碑和声誉作为评判人才的标准,那就很难杜绝个人的爱憎和好恶,必然导致贤才和庸才的混淆;如果完全用政绩来考量,又很难杜绝一些人的弄虚作假。所以他说“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资治通鉴·魏纪五》)
那究竟该怎么办?
还是应该相信制度建设的力量。就宏观层面的制度设定而言,柳宗元在其名作《封建论》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秦“有叛人而无叛吏”,秦之亡,“非郡邑之制失也”;汉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反而更说明秦之废封建设郡县之高明;唐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说明郡县制的设立可谓万世法。但是唐之癌症在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其出发点本是为了加强对基层郡县政权的督察管理,结果却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之崩溃,也可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就指出:“(唐之官制)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欧阳修指出了一个制度建设的规律: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制度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破坏。历史何以至此?顾炎武的高论可以看做是对欧阳修上述观点的注解,他在《日知录》中说:“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前人立法其实就不是尽善尽美,留有隐患,后人因循守旧,不敢彻底扬弃,只能补丁上面摞补丁,甘做裱糊匠,最后的结果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觉得问心无愧。
宋代要汲取唐之教训,所以“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这样做貌似对症下药、防微杜渐,但实际实行下来,却出现了“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以使之矣。”(宋·叶适《水心别集》卷十《始议二》) 在叶适看来,宋代的“外削中弱”盖由其国家制度设定而导致。至于他所说的“人才衰乏”问题,叶适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叶适的结论是:“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如此看来,制度愈严苛,反而愈束缚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度变迁确如按下葫芦起了瓢,总是得一利总要受一害,此消彼长。所以,相信制度不等于要迷信制度。
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西晋名家杜预说得很透,他说:“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说到底,还是荀子那句话“不患无治法,而患无治人。”再好的制度都是要人去实施的。问题是人究竟怎么去实施操作选官制度呢?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二
从九品中正到论资排辈,代代有本难念的经
选贤任能,自古是吏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怎样才能选到贤能之士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就微观制度操作层面而言,先秦时期主要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秦始皇改而实行封建官僚制,大多数官吏都是靠军功而得到爵位和官职的。在汉代,察举和征辟是当时选用官员的重要方法。察举和征辟的主要根据是被选者的乡党评论,即所谓乡举里选。问题是乡党评论的话语权逐渐被有势力、有影响的官僚利益集团所操纵。豪族大家把持话语权,他们互相勾结起来推荐亲属故旧,完全置公道于不顾,以至于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怪现象。即便有有良心的品评者,他们的话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也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东汉后期汝南地区评论人物,照例每月初一进行,称为“月旦评”,曹操当年得了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还美滋滋的大笑而去。
汉代亡于宦官干政、外戚专权,到了曹魏政权便吸取教训,魏文帝曹丕诏令“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规定宦官外戚一概不得干预朝政。为了矫正察举、征辟的弊端,曹丕还采纳了礼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中正制杜绝了以往凭着少数人一言就使人飞黄腾达的现象,要求中正官根据家世、才能、德行,察访与被品评人同籍而散在各地的士人,把人才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此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九品中正制的好处是使任人以官更规范、更便于根据评级的不同而确定官级,给吏部的操作省了不少事。所以起初的积极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晋书·卫瓘传》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但是九品中正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那就是品评的话语权掌握在一些在职官员手里,而且这些人还是士家大族。这些士家大族对人物的评定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以门第为标准,导致九品中正选官的流弊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现象。东晋之后,士族与庶族的分野进一步被强化,“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南朝齐规定:“甲族(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族)以三十试吏”。(《文献通考·选举考一》)门阀士族的势力鼎盛期在东晋江左百年间,此后在南北朝时期日趋衰弱,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隋唐时期的门阀士族仍然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一直到唐末,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韦庄《秦妇吟》)到朱全忠(即黄巢起义降将朱温)将包括被他称为“衣冠宿望难制者”的裴枢在内的三十余名朝官斩杀于白马驿,投尸黄河,标志着门阀士族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
在南北朝时期,伴随着门阀士族的日趋衰弱,羽林武人凭借着乱世军功迫不及待希望取得为官的实权。然而僧多粥少。到了北魏时期,为了解决官职少,应选者多的矛盾,吏部尚书崔亮奏请为停年格制,即不问才能,授官一律依年资分先后。凡有空缺职位,不问贤愚,择停解年月日久的优先叙用。这就是所谓停年格。自西汉以来,就把任职年资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但当时并不仅仅用这一种办法决定官员的升迁。至北魏崔亮始,论资排辈堂而皇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崔亮提出论资排辈是囿于当时武人乱政而不得已为之。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利益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耐人寻味的是,崔亮的继任者甄琛等人“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顾炎武说“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权宜之计为什么会被后世沿用下去?
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组织部长(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够,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只要熬够年头就可以提拔任用。那些被埋没在低阶层的官员,全都称赞崔亮贤明能干。
崔亮的外甥,最高监察署军事参议官(司空咨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您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再去克己苦修、注重名节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刻,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个人才中只有六七个被任用。今日所有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谋划,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享一个官位,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司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司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后世的主管者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答案恐怕就在“利其便己”四个字中。
论资排辈尽管限制了人才的任用,但是别忘了那些受益于论资排辈的庸才们的势力。没有这个制度,他们恐怕永无出头之日。千万别小瞧了他们捍卫既得、即得利益的决心和能量!对于具体负责选官的组织部门来说,这个办法“简而易守”,比较好操作,对于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又认为这个办法“要而易行”,比较好执行。基于这些考虑,后任的为政者在历史惯性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乐得“踵而行之”,沿着前人的脚步走下去。由此,明知是一副慢性毒药,大家仍然乐此不疲,似乎越喝越上瘾。
唐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又创“循资法”,官吏“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是铨授(晋升)”,结果是“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朝又实行“磨勘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年限一到,就能照例升官。至此,论资排辈的规则也越订越严密了。
对论资排辈用人制度的弊端,宋代的孙洙专门著有《资格论》予以口诛笔伐,他说自古以来提出的各种选官制度,从始至终一无是处的就是论资排辈!贤能之士被压制而身居下位,是因为有论资排辈的阻隔;在其位而不能善谋其政者,是由于论资排辈的牵掣;读书人寡廉鲜耻的越来越多,是为了在论资排辈中争个好位子罢了;老百姓被虐政暴吏困扰,根本问题是论资排辈的庸官酷吏太多了的缘故。国家大事之所以弊端横生,文武百官之所以颓废懈怠,国家的法度之所以頹烂决溃而不能匡救,根源都出于论资排辈的弊政。孙沫认为,好的用人制度应该做到“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资深久考者为优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无奈。“位不度才,功不索实”的现象反倒代代常有。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三
抽签抓阄何以成为选官的办法
更耐人寻味的是,到了明代,选官制度又比论资排辈堕落了一大截。
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明代选官起初用过抓阄的方式,后来吏部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的司长(文选员外郎)倪斯蕙向上司提出了抽签的办法,当时的吏部尚书李戴就准备报请皇帝批准照此执行。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孙丕扬出任吏部尚书。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上说他个性倔犟、刚直不阿,同僚没有人敢托他的人情办私事。然而就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把倪斯蕙提出的“掣签法”进一步完善并正式实行开来。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更有意思的是,孙丕扬用抽签的方式选官,却得到了当时朝野上下的交口称颂!宫中的权宦们认为这样做是最公平的( “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
这样一个近乎荒唐的做法为什么在当时得到这样的评价?孙丕扬为什么要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明代是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的最高峰,朱元璋连为他打工的丞相拥有的权力都不能容忍,杀掉胡维慵后干脆连丞相也不设了。《明史·职官志》总结明朝的行政权归属,说: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天下事就由各部尚书负责处理。大学士当顾问,皇帝自己做决定。这时候的大学士很少能参与决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的老师的资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经在六部尚书的地位之上了,内阁权力也从此超过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严嵩用事,其地位已经赫然为真宰相。不过,内阁的拟票权,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所以历代宦官为祸,以明朝为烈!明代的大太监们在权力的中心玩出了名堂,前有把皇帝忽悠到做了瓦喇人俘虏的王振、继有富可敌国的超级大富翁刘瑾,当然还有“九千岁”魏忠贤!这些人在太监史上可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狠角色!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文武百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扬光大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可见孙丕扬同样用心良苦哇!
曾经当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在他的《谷山笔尘》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的镜子还能照见容貌,折断了的秤杆还可以秤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现代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 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从孔圣人的教导的高度出发,径直联系到天下兴亡。顾炎武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历史的倒车竟然越开越滑向黑暗的深渊,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回到欧阳修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论述。大唐王朝之所以形成了盛世,是因为唐太宗在位时制定了一系列严密而有效的制度。欧阳修在总结唐朝官制的沿革时说:“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新唐书•百官志一》)在这段精炼的论述中,欧阳修揭示了官僚制度的几个重要原则。他首先说明制度的设计必须精密。只有制度精密无疏漏,执行起来才能简单易行。如果制度不精确,不严密,则执行的人就无所依据,而要靠自己对“道”的理解,即兴发挥。发挥得好,皆大欢喜;发挥得不好,则难免误事,给国家带来损失。第二层意思是说,每一个王朝在开始时都想修订制度,申明法纪,渴望建立不朽的法度。而往往导致“交侵纷乱”结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的国君不能严格按照制定好的“大政方针”执行,遇到问题不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随意突破国家以前制定好的法度。这样做的后果是国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官越设越多,效率反而越来越低,“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最终导致官制彻底崩溃。
崔亮在面对武人纷纷要官做的局面时不是没有提出过解决办法,他曾当面向皇帝建议“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当时的皇帝顾虑军人造反,在建议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下,崔亮才提出了论资排辈的馊注意。孙丕扬面临的问题是宦官干政严重。当时的皇帝“不能慎守”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宦官不能干政的祖制,而作为吏部尚书的孙丕扬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徇一切之苟且”,干脆主动放弃了自己选官的职权,“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四
选官操作中的“法”与“吏”
具体到选官的实施操作,人才标准好定,如何掌握实施才算真正的大问题。如果完全按制定好的规则选官,古人则云“胶以条格,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后果?选官制度到底是怎么被破坏的?
南宋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叶适在论述选官制度的弊端时指出,吏部视选官制度高于一切,对于备选官员“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过于相信既定的死规则,就会导致“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所以他忍不住大声发问:“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禄,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宋·叶适《水心集》三)无他,制度延续的惯性使然。正是看到了制度惰性的可怕之处,顾炎武才下了如此断语:“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日知录·人才》)选官规则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少数人上下其手,徇私舞弊。为什么顾炎武说其正面作用至多发挥了百分之三十,而其负面效果却达百分之七十呢?
选官之“法”不可依,问题出在执行选官之“法”者为“吏”。“吏”即吏部具体的办事人员。
南宋大臣杨万里作《选法论》,他指出:“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吏”把选官之“法”看作是自己的“取富之源”,再好的选官之“法”也不能够成为国家的“择人之具”。杨万里指出,吏部的主要领导尚书、侍郎往往只是“据案执笔,闭目以为纸尾而已”,大多数时候,他们只知道在下属呈上的公文后面签上自己的大名。为什么会这样不负责任?朝廷制定的渎职惩戒制度不是不严厉,“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的本意难道是真的只相信“吏”而不相信“官”吗?很显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选官的规则决定了事情的发展只能就是这样罢了。朝廷的本意还是相信吏部的主要领导“官”,但选官之“法”规定连“官”也不能信。在选官问题上,说到底朝廷连自己也不相信。天子都不能信赖,更不要说“官”了,那选官之“法”由谁来实施操控呢?只能取决于“吏”。最终的实质后果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选官的话语权实质上操控在“吏”的手上,“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所以吏部的主要领导实际上只能按照“吏”的意图行事。但他们可决不承认是按照下属的意图行事,他们振振有词“曰吾奉法也”,我只是按照选官规则行事。所以杨万里才说选官之“法”的实施是“信吏而不信官”。
“吏” 究竟如何上下其手?深谙宋朝官场潜规则的杨万里做了形象的剖析。他举例说,如今有一件事情要处理,按照规则规定,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规定的很详细。下级官员把这件事汇报到吏部,按照相关规定请示部领导说按照某某相关规定应该如何如何。部领导说行。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没想到一转身“吏”拿着一张纸条又说那么办不行。既然说了不行,应该是没有回旋余地了,过不了多久又拿出一张纸条说行。说行说不行都有相关的规定为依据。关键是说行还是不行的没个准头。“何为其然也?吏也。”为什么会这样?“吏”操控的结果。下级官员刚到吏部汇报的时候,仗着所请示的事情符合相关规定,又觉得吏部的主要领导都很贤明,所以汇报工作之前不先去面见吏部的小“吏”,所以请示吏部的主要领导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再找“吏”去落实,“吏”却说‘法不可也’,按照那个规定不行。关键是他那么说,部领导还反驳不了,也就认可了“吏”的意见。如此一来,下级官员遇事不再照章办事,也不再向部领导请示,而通过贿赂“吏”以成其事。“吏”答应了,你也不能着急要结果。他要等到主要领导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再套取他们的签字画押。昨天说不行今天就说行,早上认可晚上就不认可,部里的主要领导不知情,朝廷也不会苛责。“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为什么会这样?“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
这么做的病根在哪里呢?杨万里说:“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忘了选官的根本宗旨,过于注重条法程序的严密完整性。“吏”恰恰钻的就是选官程序过于严谨繁琐的空子,以捍卫程序严谨正义的名义,找到其中不为人注意的环节大做文章,这就是他们能够永远正确,还不栽跟头的原因。问题是朝廷如果只是拘泥于程序严密,那么选官用一个小吏执笔就绰绰有余了,还用得着选天下之贤才为吏部的尚书、侍郎吗?朝廷任用尚书、侍郎的原因,绝不仅仅是让他们拘泥于现成的条法程序啊!所以杨万里的意见是“略小法而责大体”。对吏部的主要领导而言,只要明白程序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绝对非得如此,只要不伤及根本宗旨,那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决定用人行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只要不违背选官的大方向,不损害立法的大原则就可以了。杨万里认为,强调“责大体而略小法”,那么朝廷的选官就不取决于“吏”之手,导致“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吏部的主要领导才能有所作为,而选官之“法”才能逐渐革除弊病。
吏部之权在于“注拟”,也就是铨选后备干部,吏部给各级官员都建立档案,列入后备,然后才能一级一级逐级提拔选用。凡是要提拔的,就说是符合提拔任用条件,过去的专有名词叫“应格”,凡是不予提拔的就说其“不应格”。杨万里说:“曰应格矣,虽贪者、疲软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不管选拔任用的是什么人,只要他们不愧不怨,吏部的人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完成任务了。
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杨万里的结论是“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也就是说关键是选好礼部尚书,让他来精心挑选郡县两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副手,不要拘泥于条例程序等细枝末节。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迁与变异之五
循“例”与“破格”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了解,“吏”肆无忌惮的底气在哪里?
“吏”的底气来自于“例”。“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规章制度。一个单位建章立制本是好事,这是规范化管理的需要。问题是规范一旦成形,凡事按制度办,就容易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南宋吏部侍郎凌景夏说:“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文献通考·选举考》)规章制度的完善是必需的,但规章制度往往有其滞后性,一旦形成,便带来两大弊端:一是很难与时俱进;二是一般人很难弄清楚繁杂的条文,解释之权归相关部门,“有司”自然有了话语权。
从规章制度之“法”到实际施行过程中之“例”,对其演变,南宋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例行而法废”铨选之害更甚。所以顾炎武说“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日知录·铨选之害》)
《五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一个关于“例”的有趣的故事。当年宋真宗当政时寇准任宰相,宋真宗命寇准等重臣选拔一位官员任马步军指挥使,寇准等重臣刚准备商量人选,下属“吏”就拿着一本文书呈了上来。寇准问这是什么文书,下属回答这是例薄。寇准说朝廷想选拔一名衙官,还一定要先看例薄文书吗?那还用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寇准痛批:“坏国政者正由此尔!”
当年司马光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讨论新法利弊的时候曾经说:三司使掌管天下财,任人不合格罢免了就可以了,不能让宰相和枢密使等重臣侵夺三司使的权力。如今你再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什么用心?司马光说:“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宋史司·马光传》)面对司马光掷地有声的质问,吕惠卿哑口无言。
顾炎武总结传统社会“吏”何以上下其手成为弊政的时候指出:“胥吏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解决这一弊政的办法,他说只有“”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日知录·都令史》)顾炎武的说法也许过于理想化,也缺乏可操作性。 那么,如何才能选到真正的人才?如何才能打破任人以“例”之弊政,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法”和“例”属于常规的选官办法,不可能尽废,比较可行的办法便是“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也就是以常规化选才为主,常规化与破格选才相结合。清代有循吏之称的名臣陆陇其提出:“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进,以守选法之常,而英流间得超擢以登,以通选法之变。”(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铨选之害》)这样做的好处,陆陇其说既能堵住中等庸才越级而上的可能,又能给真正的英才提供破格提拔的机会。这一点应该是许多人的共识。清人姚莹也认为:“登进之法宜有常格以绝奔竞之门,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捉非常之用。”常规之法管寻常之才,非常之才用非常之法,只有这样,才算选贤任能的理想选官之法。
我们常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人才要想脱颖而出何其不易!龚自珍认为,清朝官吏制度品级设置繁多,阶梯难熬,一个人从30岁做官,一般需经30~35年方可到一品,造成“贤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的局面,这是朝廷“无才相”、“无才将”,国家贫弱的主要原因。所以他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要想打破条条框框选人才,当然首先要打破固有观念发现人才。如何辨别对待人才,这又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清人姚莹的论断就很高明,曰:“夫有雄材绝智,抱济时之具者,此其人类不能斤斤于言行称誉之间矣,有不为乃可以有为,释其小乃可以见其大。举世不觉而独言之者,必有观时之识;举世共趋而独不顾者,必有经远之谋。接其人,察其议论,毋以资格相拘,毋以毁誉惑听,是在执事者之鉴择矣。夫阔大者多疏,沉毅者多略,高明者多傲,英迈者多奇。观其病则其美可见也。若夫谨言曲行,与众俯仰,岂所望于国士哉!”(姚莹《通论》)在姚莹看来,发现人才就不能循规蹈矩,要善于在不同于常人的另类中发现人才。能具备先见之明和做出先人之举的,必是非常之才。关键是“毋以资格相拘,毋以毁誉惑听”,不能用常规常格框住这样的人,更不能被流言蜚语迷惑了选才者的视听。非常之才也是人,他们也许还有常人没有的这样那样的毛病。姚莹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观其病则其美可见也”,对于非常之才而言,如果能正视其毛病,自然能发现其常人不及之美。一方面要求人才“谨言曲行,与众俯仰”,一方面又想发现无双之国士,那怎么可能呢?正如清人顾嗣协诗云“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不拘一格降人才”,需要多元的人才观和多维的选才方式。宽松的成才环境和多维的选才方式,才是造就人才发现大才的根本之道。